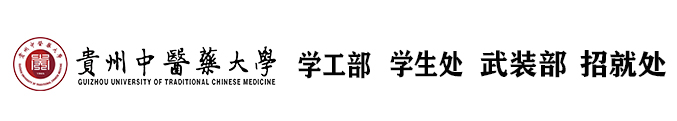认得几个字?面对这个看似幼稚的问题,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难记、难写、难读的生僻字。希望通过汉字为大家打开传统文化之窗的“汉听大会”,今年也把重点放在了古籍里的生僻字上。然而,在汉字研究专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石定果看来,认字,无论从工具层面,还是从文化层面,更应该关注的都是常用字,而非作为少数人专业的古籍里的生僻字。
她解释说:“作为一种文字的汉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在语言和文字之间,语言是第一性的,而文字是第二性的。道理很简单,所谓语言,就是我们用口来说,人类有了社会,就有交际,就必须有语言,而只有语言高度发达时,才可能产生文字系统。”从这个意义来讲,所谓生僻字,就是随着这个字记录的语词退出交际平台、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自然而然变成了“死字”。此外,从汉字演变的历史来看,现代汉字也是古汉字逐步简化、符号化、规范化的过程。比如,甲骨文中,“龙”字和“凤”字的写法都有五十多种,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逐步有了一种大家都认同的约定俗成的写法,其他写法自然就被放弃。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有的字“死”了,有的字“活”了,有的字“死”了可能还会“活”过来,有的字可能永远“死”了,这就是汉字演变的自然规律。
至于工具层面之外,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石定果认为,常用字同样是一部文化史,“每个汉字都是立体而非扁平的,不是光听写就够了,汉字的结构、演变,一点一滴中都有丰富的文化色彩。”她举了一些最简单的例子:镜子的“镜”很简单,但它反映了古人是用铜作为镜子的,而不是现代的玻璃;篇章的“篇”、书籍的“籍”,之所以是竹字头,是因为古人是在竹简上书写的;药,为什么是草字头,因为最早的药物不是化学药物,而是神农尝百草的草药;“纯粹”,为什么分别是丝字旁和米字旁,因为“丝不杂为纯,米不杂为粹”。
那么,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否一定要借助数量庞大的生僻字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以历代文学经典的用字量回答了这个问题,《论语》使用单字1512个,《孟子》使用单字1959个,文白结合的大部头《红楼梦》也只用了4462个单字。石定果的观点更明确:“老舍的作品都是大白话,一样是经典。好的文学作品,依靠的是文学修养、实践阅历以及人文情怀。即便就语言本身的丰富性而言,也在于词汇量和阅读量,而非汉字量。”
台湾作家张大春在《认得几个字》一书中曾写过一句话:“之所以误读、误写、误以为是,其深刻的心理因素是我们对于认字这件事想得太简单。”的确,那些我们听说读写过无数次的常用字,何尝没有自己的故事和历史,何尝不需要我们仔细品味它们背后生动而丰富的文化史?